书橱里藏着一只黑蝴蝶。三十个年头了,它一直都在那里。与它毗邻的,是只白乌鸦。
白乌鸦总以仰视的目光去望黑蝴蝶,望它飞出书橱,翩翩地舞着,时而栖息书桌,时而停留茶几,有时,也立在窗台上。
今早它又飞了出来,落在冒着热气的咖啡杯旁。我看它,它也看我。心就咚咚地跳。然后双手合十,二目微闭,黑蝴蝶就不见了,却幻化出一位老人,满面沧桑,目光如炬,照我心中一片光明。可睁开眼,老人却不见了,黑蝴蝶还是黑蝴蝶。
近些年,我的书房里,常常上演这样的一幕:睁眼黑蝴蝶,闭眼一老人。似有千言万语,却又相对无言。
难道只能以这种方式相见?答案:是。这是永远的、唯一的方式!
这位老人就是诗人王辽生。
他曾以黑蝴蝶为题赋诗,还以黑蝴蝶为其诗集命名。《白乌鸦》是我的第一部小说,我也以其作了小说集的名称。《黑蝴蝶》和《白乌鸦》在我的书橱里毗邻立着,像大手牵小手,像师长带学生,像孩子跟着大人学步。许多年来,我就以这种方式,向王辽生老师致敬。
和王老师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。实际上,我们的第一次“相遇相识”并没真的见面。那是1983年9月25日晚上,徐州首届青年文学讲习所在少华街小学举行开学典礼,先生没来,却让人带来了他的一首诗——《文讲所开学有贺》:
心系社稷魂运笔,意在江山一碧。问中华来日,云正风清,日辉月丽,座中谁染墨一滴?
贺诗诵罢,掌声热烈。掌声中,我想像着这位大诗人的模样,一定是高大伟岸,目光炯炯。声音也定如洪钟一般。又仿佛觉得,诗中的激情文字,就是冲着我说的。
后来,一帮子文学青年组织文学社,请他做顾问。其时,他以55岁高龄去了新疆石河子,担任《绿风》诗刊副总编辑。我把聘书寄给他,旋得他的回信:
刚良:聘书收到。顾问纯属挂名,对于你们的发展飞升并无大意义。不过你们既已热情相邀,我总还是要竭尽心力的。好在我逗留边地不会久长,或者明年初春,或者今岁年底,我即归去,当能时常相见也。
实际情形是,你们诗社的水平还不行,在全国上千个诗社的汹汹大潮中,你们当小心被拉下。没有别的办法,奋斗不息而已。
信的落款是1986年6月12日,到我手上已是一周以后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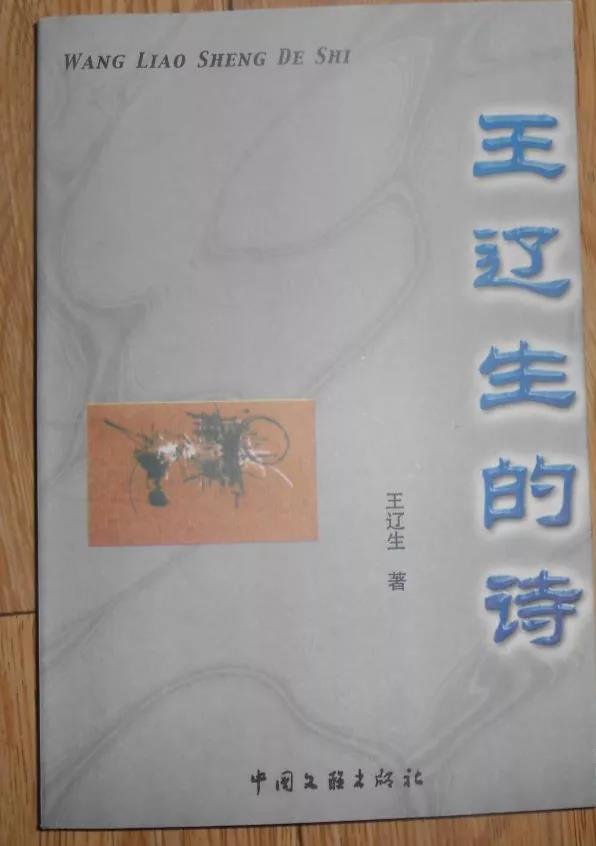
一个蹒跚学步的文学青年,捧着大名鼎鼎的诗人、师长、前辈的亲笔信,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!但看到那句“你们诗社的水平还不行”时,心里咯噔一下,仿佛什么事情没做好,在家长面前垂首挨训一样,好一阵子没缓过劲儿来。在此之前,我还陶醉在文学社的辉煌成就中,一句“还不行”,让我不得不想:怎么就不行了?
说实在的,那时还真是觉得我们的文学社是“很行”的!
徐州的报纸就不说了,《新华日报》刊载的《扎根家乡沃土,讴歌时代风貌——云龙湖畔有一群文学青年》一文,也介绍了文学社的成绩,其中还有这样一段:“杨刚良在《雨花》上发表的《牧归》、周珞在《青春》上发表的《嘉陵轻骑》都是较好地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。”另外,上海的《文学报》及香港的《中报》,也报道了文学社“出成果、出人才”的“业绩”。都“大报小报”了,都《雨花》、《青春》了,咋就不行了?
现在想想,我是多么幼稚,多么鼠目寸光。而王辽生老师又是多么的真诚!
以后的交往就多了。所谓的多,也只就那时的条件而言。没有手机,电话也只个别单位才有。又新沂、徐州两地住着,交通也不方便,想见上一面,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我们还是去了新沂。那是1986年10月10日,两辆摩托驮着4个人,出城往东奔新沂。王老师不在家,说到淮阴参加酒乡行诗会去了。两个多月后二次拜访,才有幸得见王老师。翻检记忆,他家的房子不大,屋中间有个火炉,于美华阿姨在炉上为我们煮了羊肉面条。天已经很冷了,我们却吃得周身温暖、心里滚烫。也聊了许久,听他讲诗、诵诗,甚至还听他唱《心中的玫瑰》。他那瘦小的身躯,竟蕴藏着那么大的能量,歌亮话稠,抑扬顿挫,激情澎湃!
去几百里外的另一座城市访师,在今天看不算什么。但在三十多年前,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。前不久在新沂见到陈诗人广德,他还提起我们当年的壮行,说如何骑着摩托车去新沂,和他有过至今难忘的会面。
那时不独见面不易,电话也不方便,通联方式多是写信。至今,先生的许多亲笔信我还珍藏着。
写信向他讨教,回信也绕弯子,说:“你的诗赘句太多,应注意文辞精简,一语入扣。”又说:“你的诗在句式上比较讲究,而在整体上稍觉浅显,必须有火有血,对思考的人生作深入的掘进。”也有鼓励:“在《徐州矿工报》上读到你的诗,觉得亲切,你始终在不倦追求,如能破壁,将有所为。”“退稿是常事,不断奋斗为好。你还需不馁,写下去,投下去。”
我不记得王老师夸过我的诗,也慢慢地知道我不是这块料。这是我后来不写诗的原因。他的鼓励,却使我坚持着对文学的追求,保持着写作的兴趣。

1989年1月11日,王老师自新沂来徐,来前写信告我行期,我便往蓝天旅社拜访,请他看稿,听他指教。分别时得《诗人的自白》一书,书中有他的文章。他还在扉页上写道:
在失败与成功中挺进,必能获得充实的人生。愿刚良终成大器。
如今终于成“大”(年龄),却不敢言“器”。
王老师对年轻人从不放过任何鼓励、提携的机会。《徐州矿工报》1989年5月16日的煤海副刊上,刊有一则文讯:
“杨刚良的新作《永恒》,在‘首届全国箫韶杯文学大奖赛’中荣获优秀作品奖。该厂陈再华的《射门》获《芒种》首届万家诗会希望奖。局工会刘欣的《地下蘑菇园》获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、《中国煤炭报》联合举办的‘改革大潮中’征文首奖。”
这则文讯便是他写的。
他还于1988年在新沂主持了《走向未来》新诗函授中心,写信让我参加。我借学习的机会结交了许多文友,也聆听了许多大家的点拨教诲,开阔了眼界,汲取了许多益于成长进步的文学养料。
我们的通信除了谈诗说文,有时也说别的。他在1989年5月2日给我的信中说:“我妻于美华今日体检,高压160,低压99,大约患了高血压症。你是医师,对此恐怕有些疗救主张。你若能找到一点对症的药物,可请费心一顾,并盼能在5月7日至9日我在二招开会时送给我。当然,若你处取药困难,则只将何药告我亦可了。”
对我来说,这不算事儿,何况又是老师交代的。
有时来信也说某某书好,可以购来一阅;某某人的诗好,可以寻得欣赏学习。
王老师再也不会有信给我了!却有一只黑蝴蝶,永远在那儿,静静地望着我。
他在《升落只缘情》一诗中说:“西天之穹,飘飞着一个黑色生命……火中飞出的那只蝴蝶,黑得叫你动情。那只蝴蝶的雄性烈血,只为你而沸腾。”
诗中的“你”,肯定指的不是你或我,其指向,读了诗你才能知道。
有人说新沂有两座高山,一座是马陵山,另一座就是王辽生。其实,他何尝不是徐州江苏乃至中国艺术高原上的一座山!
谢冕说王辽生是一位“生平坎坷的诗人”,柯岩说他是“当代一个重要的诗人”。柯岩在1979年召开的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有个大会发言,特别提到了王辽生,还现场朗诵了他的获奖诗作《探求》:
如果人人都无所探求,
真理何日捕获?
但愿为探求而受难的人,
宽慰于演完最后一幕。
……
毛发不经流年磨,
确乎白了许多;
心没有白,血没有白,
且捧给四化的滚滚雄波!
……
呵,一如这波涛不可抗拒,
探求的权利不可剥夺;
让我们高举探求的刀剑,
叫全球惊看中国!
朗诵赢得掌声经久不息,无数人眼含热泪。柯岩说:“因为他说出了所有代表的心声,是那个时代那一大批经历了苦难却忠心不二、矢志不移的知识分子典型时代的典型心情。”
王辽生说他的诗是“沉郁的锯琴”,说:“我活着并非奇迹,奇迹应该是死得豪迈。如无意间点燃一个青春,如闪电般划破一个时代!”他还说:“谁今后看见黑色的蝴蝶,那便是我的灵魂翩翩。”
一位生平坎坷的诗人、一位重要的诗人,高举着探求的刀剑走了。
中国诗歌的星空里,人们永远都能看到,一只黑蝴蝶,飞,飞,飞……


 苏
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