泥马度,本名李旭。从事杂志、图书编辑工作多年,现为文联专业作家。著名长篇小说多部,主要有“自然帝国•四季书”:《山川易》(搜狐签约作品)《山云飘向帝国》(金城出版社);《草药帝国》《鲜花帝国》。畅销书《烧烤水浒》《红楼梦的秘密》等,文史专著《梦回汉唐》入选中国作协国家重大工程出版工程,作家社出版。出版六万行《汉史诗》等诗集七部。在《十月》《中国作家》《诗刊》《散文》等各大报刊发表作品数以千计,上百篇首入选多种选本。发表、出版作品四百万字。

《诗歌王朝》序言
邹 静 之
远方的村庄里诞生一些真正热爱诗歌的人,像一种古老的梦想。村庄是神创造的,也注定有磨难。在那里更与命运短兵相接。生活也许并没有埋没人,只是把诗人的“诗”字掩掉了。
梢上一枝乌鸦一枝喜鹊各自啼叫着“苦难,苦难”、“欢乐,欢乐”。
李旭(泥马度)迷恋于冬日村庄的景色,呜呜的风徘徊在屋外,他独自一个院落点亮灯,整夜整夜地读书,写诗。他说自小更迷恋于冬日长夏说鼓书的夜晚。有一扇柴门,那是朝向过去直至洪荒。总有人永远为此门出神,“魂梁游走了”。
他第一次完整地读到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,是在乱哄哄的书店,竟然呆站在那儿直到看完,涌出泪滴。
他白天劳动,就像一个被庄稼领着走的人,家里人常说他人在干活,心不知跑哪儿去了。他希望不要太嘈杂刺耳的声音就行。但生活一再像失火,烧着人的眉毛。九十年代的农业是很苦的。他忍受了过来。只有像个呆子,呆头呆脑才能做成一件事情。
在《美文》上,李旭曾写过一篇《呆鸟》。这种鸟,常常呆呆地站立着,在大地上一动也不动。即使迎面汽车也无动于衷。它在出神,出神到和世界相忘的地步。心在别处,忽略此间此时所谓巨大变化。没有人能够叫醒他,他像这样的呆鸟,呆于心中漫长的构想。但接触他的人都知道他并不木讷,对于崇敬的过于诚恐无措;对于不满的则像一棵花椒树扎满周身锋芒站立于地面之上。朝圣和愤怒都会使人“发呆”。
他并不后悔自己当初只迷恋长诗,而不在意短诗写作。太多的话要说,就像村里的一个人有了外心,就有了长途跋涉与探险。长诗,对于汉人少有成功先例。这需要诗人自己的路遥和马力。沿着地,一路渡河,能走多远就多远,能走多长就多长。一个人黑灯瞎火地摸索,成功是很多人,失败却只属于一个人的,那他心中的光是什么?一匹老马是否识旧途?返回历史的真实之地去?
平静的生活下掩蔽了很多人的历险与色彩,只是有人不说,有人一定要写出来。土地有言或无言。九十年代,李旭的生活节省得几乎不投稿,不浪费一枚邮票。1994年他积蓄了一点钱到京城找我,见面说不出话来,带了一厚叠诗稿,他只说让我看看,不可能发表的。他对自己很是失望,忧伤。他喜欢我的《与牧羊人》,贴在乡下书桌前,心里多少年都流淌着此诗旋律。苦闷时,他一遍遍地读圣经,当时他写了《耶利米哀歌》。我给了他一些安慰和鼓励。又送他一沓稿纸,在他本子上写了段话。
在地里无论怎么耕耘,一个农民又能有怎样的收获呢?李旭说他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收获什么。种自己的地,有了长势,是理所当然。天种天收的。人能做什么。
我们能感到他心里有一团火,这种火势使他诗歌。同时使他焦虑。他有时莫名地脸被烧得通红,破了。
这本诗集只有四首诗。其中《魏风》,写出几种基本元素的互相生克。风水火土金木,此篇彰显“风力”浩荡。元素因成为史实的血液,而没有成为语言暴力,相反造就语言的气势。
历史意识在当代诗人中普遍缺乏或浮浅,而这部诗集中却过多弥漫逝去的时光。时光有真假。
历史对人或是一只猿,对面不相识的很多,哪怕是置身其中。有遮蔽就有发现。风吹开草底也吹开文字。跃入并漫游长河,捕到龟相负诗的人是对汉诗王座的一次追寻和叩门。但只是闪电一倏即失。路仍茫茫漫漫,未知。历史并非过去,向后,《耶利米哀歌》是“冬江水寒鸭先知”,眺望,穿透时光的水面,来去兮,有它的火焰和流动。历史的河流并非教科书,一半是天然,人工“运河”只是一种说法挖掘。《一》里有一些“动物”,它们蕃息在河流的九曲十弯处,有各自的真实和秘密。
不能说怎么如此这般只能是摸索,听下回分解。对于一匹泥马,路途迢迢,并河流不断地横在眼前。
一只呆鸟,像扎在花椒树上蝶翅状的嫩叶,不声不响地成长。一只呆鸟,落在历史课文里,像一行行漆黑的汉字延伸下去。
直觉和缜密的体系
大卫
李旭曾有好长一段时间见朋友便谈《红楼梦的秘密》,酒桌成了他石头城逐鹿的场所。无疑他的话题很有价值,对这部天才巨著,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,有兴趣的大有人在,真理不辩不明。
他有石破天惊的一个个发现,每抛出一个观点,朋友们都会和他激烈争论。他喜欢每一个质疑和挑战,总是能说服反对派,成为他红学的支持者。对红楼久有研究,写过多部专著的作家申维教授由质疑者变成铁杆粉丝,甚至提议成立李旭红学研究沙龙。
必须承认李旭的论据非常充分,一百年来,竟有这位诗人学者找到最靠谱的、关键性的红楼梦研究材料。他的材料不是自己发现的地摊、潘家园货,而是无可争议的公共材料。这么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,为什么偏偏由这他发现,而不是别人?要知道研究红学的官方、民间人士如过江之鲫,这么长时间,为何众人都遗珠,有眼不识泰山呢?
这就是缘分,冥冥之中的一种心心相印,精神对应。所谓鸣鹤在阴,其子和之,虽隔四五百年的时光尘埃,也难阻隔诗人之间无师自通的心灵解码。
李旭以雄辩的力量,自成体系,环环相扣地论证石头记的作者本是四海宗盟钱谦益。钱谦益是被满清王朝抹黑、封杀的一代宗师。
在一个清廷戏走红爆棚的岁月,钱谦益必无出头之日,也无人注目,只有漫化式的轻狂辱骂、不屑。
但李旭不一样,他是严肃的史学者,他是六万行《汉史诗》的作者,他对明史特别是明代文学史有深入的研究,并有公认的成果。在《诗刊》做编辑时,他就常常语惊四座。
被迫降清的人极多,钱谦益是被逼潜伏到曹营清室。他本来是和妻子柳如是相约投水自杀的,但临死那一刻他顿时清醒了。他担负着复兴国家的重任。他不是寻常之人,是崇祯临终前赋予重任的督帅,是整合天下不可缺的精神盟主。同时整个儒林都知道,国家只要有钱谦益在,就没有灭亡。因为他是第一史家,只有还有史传,天下就没有灭亡。
死容易,活着肩挑复国大任太难了。钱谦益选择的是最难的那条路。他被清室抓捕两次入狱,甚至面临夷灭三族的危险。
他降清只有几个月,清军刀支着脖子让他撰写明史,他只字未写,而是挂印南奔。
这样的人,被清廷骂为非人类,恰恰就有他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史学家陈寅恪非常了解钱谦益,因此曲笔写了80万字的《柳如是别传》。其实就是为钱谦益翻案。这是大师之间的心灵沟通,因此陈氏说某种程度钱谦益的诗歌超过了杜甫。因此才有红楼梦里一系列杰出、分明打有钱氏及妻子柳如是及盟友的诗歌烙印。
钱谦益的世界打开了,在李旭面前,他不仅重新发现一个南明史,更重要的发现《石头记》的原作者大量资料,铁证。再也找不出这样稳丝合缝的证据了。他写第一篇历史随笔极为精确地论证出青埂峰、大荒山的出处,看后不由得不信服,钱谦益就作者。而这对李旭的研究来说仅仅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,他以横扫千军之势,连珠炮一般轰炸出近四十万字的红学新体系。
他颠覆了一个“旧世界”,同时也呈现一个新世界。他所著的《红楼梦的秘密》,为读者呈现一个霍然开朗、茅塞顿开的水帘洞。他解开扬州耗子洞所有秘密,终结了一个红学的无底洞。
李旭的史学功底,来自诗人的灵性、天赋,无师自通。有一次,他看见我的案头放着三本《中国人史纲》,这是台湾作家柏杨的著作。他拿起来对我说,这是一部硬伤遍野、非专业的历史误读,与其说是史纲不如说是作家的历史随笔。它的价值在于,作家的文笔好,个人观点新鲜,有激情。他最后对我说:“你随便翻一页,我都有可能指出他的不足、硬伤乃至荒谬。”我不服,试了几次,果然他都他说中。杂文家梅桑榆解释说,这么多错误,可能是柏杨在狱中写,没资料查。李旭说狱中有资料供他查,他出狱后也有足够时间修改,勘误。主要是他对历史主体没有把握,所写的东西是瞎猫去碰死老鼠的,没有专业的精神。
他曾在一本书里说,中国的历史至少有一千年其实是由诗人创造的,诗人是历史的灵魂。他又说最初是史巫不分,就是后来的翰林院,也是将诗人与历史融为一体。
他对历史认知往往来自直觉,他自小读红楼梦,判断所谓的曹雪芹不可能是原作者,也是来自诗人天生敏锐的直觉。
灵敏的直觉经过多少年史学的沉淀,又经过他自己近十部的长篇小说的创作经验与感悟,他胸中的红楼基本上已尘埃落定。
所以说《红楼梦的秘密》这本书,还原了该书是史家、诗家双重的史诗绝唱的庐山真面目。经过他的重新阐释,《石头记》水落石出,脱离迷津故瘴,真真地瑶草拱壁,汉家的日月重开。
李旭已出版作品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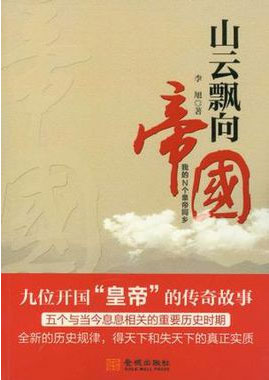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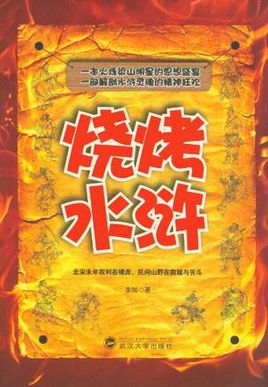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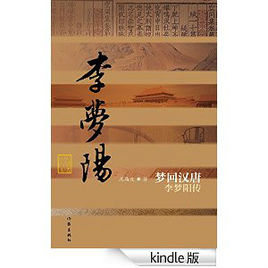


 苏
苏